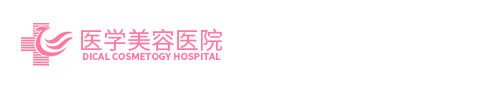华体会新闻
史学家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名人叙事”,将其生平作为构建历史事件与历史意义的载体。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依次说明“本纪”“表”“书”“世家”的著述旨趣后,以“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点出“七十列传”的取舍标准,即能入列传者需秉持正义与道德、豪迈洒脱,且能把握时机顺势而为、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虽然司马迁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是他的“列传”也被后世认为是树立起了对不同类型人物的评价范式,其中尤以圣贤的形象最为典范化。
古代哲学中的“名实之辨”则塑造了中国人的名人价值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必也正名乎”,强调“名正言顺”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战国末期荀子在《正名篇》中提出“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意思是一听到名称就知道它所代表的事物,这就是名称的作用。两位儒家代表人物都把“名”和“实”的一致性视为重建当时社会秩序的前提,但孔子是以既定的礼制之名去匡正变化了的现实,而荀子是根据变化了的现实重新“制名”。后世将儒家相关主张概括为“名实相符”,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实践和对道德义务的认知,也成为了中国本土语言学和逻辑学发展的基础之一,更是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伦理。中国社会强调“表里如一”,反对“名不符实”,认为“名实”统一是社会信任的基石,即是受此影响。
而在西方传统中,名人的定义是那些“因被广泛熟知而知名”(known for his well-knownness)的人。早期名人(celebrity)诞生于宗教的封神或政治的加冕。19世纪英美大众报业的崛起和通俗新闻的兴起,使得成功人士的私生活成为受读者欢迎的信息来源,也催生了“名人新闻”这一新闻类型。20世纪20年代,美国移民潮打开了潜力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名人的构成从生产领域的商业、科学精英转向消费领域的娱乐、体育明星。文化娱乐业的兴盛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名人迅速展现出商业价值。名人不仅能为商品代言,甚至自己也能成为被售卖的商品,成为资本主义供需市场中的一部分。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真人秀”(reality show)类电视节目,开始打破名人的壁垒,使得普通人(素人)也可以在有“剧本”的节目中展示真实(或表演出来的“真实”)的一面而获得海量关注和拥趸,这就让“名人”的范围从遥不可及的偶像拓展到你我身边的“真实个人”。千禧年前后真人秀节目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大大加速了普通人的成名流程,“一夜爆火”的情况屡见不鲜。观众通过投票等方式参与对真人秀中选手的培养和塑造,使得“名人”的成名逻辑从拥有某种“血统”或“专业成就”,转向“流量认可”,这一过程重构了名人的定义以及名人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
网红在英文中对应“微名人”(micro-celebrity),或者“互联网名人”(Internet celebrity)的说法,显示出对“名人”概念的承袭与演变;有时也和“在线有影响力者”(online influencer)通用。这三个概念通常都被翻译为“网红”。学者特蕾莎•森夫特在2008年的著作《镜头下的女孩:社交网络时代的名人与社群》中首次提出micro-celebrity的概念。她的研究对象聚焦于类似MySpace平台上的通过网络摄像头进行直播的女性群体——“镜头中的女孩”(camgirls),强调其通过“日常表演”构建“可接近的名人形象”,是一种非传统名人的表演性的自我品牌构建。随后,爱丽丝•马威克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对网红的研究从早期的网络社区拓展到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这样的Web2.0社交媒体平台,并结合硅谷科技文化的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分析网红如何将社交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微名人/网红”的概念很快得到广泛接受,被应用于对那些通过博客、网络视频、社交媒体等在线平台,积极地将自己的生活和个性进行品牌化,并以此吸引特定受众关注的个体的分析上。
例如李子柒最初只是一个分享乡村生活的普通女孩,通过镜头记录和呈现宁静美丽的田园风光,以及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打动了无数观众,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者。而姜逸磊(Papi酱)虽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但也是以一个普通毕业生的身份开始,凭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系列原创短视频,幽默而犀利地吐槽日常生活和社会现象,引发观众广泛共鸣和自发传播,从而走红。类似出身的网红还包括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讲解科技知识的“何同学”,来自清华大学、用生动实验普及科学原理的“毕导”等。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与“景观社会”概念,常被援引来探讨当下以影像和符号为主导的社会现象。德波将“景观”定义为当代社会中的媒体、广告与消费文化构成的视觉符号系统。“景观”使真实世界沦为简单的图像、将影像升格为真实的存在,通过制造虚假的满足和自我选择的幻觉,使人们变成消极的观者(spectator),将社会关系异化为对影像的被动凝视。“景观”的概念是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概念、拜物教理论的进一步补充、深化与抽象。它也承袭了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观点: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劳动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劳动不再是生产物质商品的活动,而是生产能体现社会差异的符号。
网红主动参与“景观”的生产,通过精心策划的视频、图片和文字,将自己的生活、才华甚至情感转化为可供消费的“景观”。网红能生产什么,不如能展示什么外观来得重要,脸、身材和情绪都成为了生产资料。他们呈现的日常生活往往经过美化、滤镜以及剧本化的构建和剪辑,创造出普通人真实生活中缺少的或不能实现的“完美”,满足了观众的窥探欲、娱乐需求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例如,许多探店网红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美食和环境,往往比实际体验更为精致和诱人;美妆网红则可能过度使用滤镜和修图,夸大产品效果。受众则欣然消费这些“景观”,其欲望和喜好被隐形操纵,却鲜有反思。
仅仅有美化修饰的内容还不够,网红生产的这些内容终究要服务于精心设计和维护的“人设”。在网络注意力争夺的过程中,网红有着多样的走红路径,可谓“各显神通”:有的在垂直领域持续深耕,输出细分领域的高质量内容,精准吸引粉丝群体,建立起权威感和专业性,但这条路是最需要专业技能的;有的则通过提供令人向往、引发共鸣的生活方式,打造鲜明个人特质,吸引粉丝喜爱和关注,粉丝也从中获得了情绪价值和生活能量;也有网红在全民关注的突发社会事件中脱颖而出,伴随事件的“病毒式”传播获得海量关注,并在流量高峰后维持住了部分关注度;还有的网红在电商直播中,通过高超的销售技巧和对直播节奏的掌控力,促进真实消费,吸引海量消费者追随,例如李佳琦、董宇辉等“现象级”主播。而无论通过哪条路径成为网红,其中都离不开鲜明的“人设”打造。
网红现象的出现在技术上受益于发达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强大的算法推荐机制。在平台社会中,数字平台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交、信息获取和消费的重要场所。平台算法根据用户的行为数据(如观看历史、点赞、评论、分享等)分析其兴趣偏好,并将相关内容精准推送给用户。在大众传播时代,内容离开媒体后便进入传播的“黑箱”,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其效果,以及是否能触及其目标受众。而在社交媒体时代,算法推荐机制完成了平台上内容与感兴趣者的火速对接,使得任何有传播潜力的话题都获得了“光速”传播,实现了“病毒式”传播效果。只要内容够出圈,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也能因此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曝光和关注,从而成为网红。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过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概念,指的是社会群体或个体所拥有的,被认可和合法化的声望、威望、信誉、名誉等非物质形态的资本。布尔迪厄还提出了“资本的转化”的命题,指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等不同形式的资本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交换和转变。网红正是通过优质内容、独特人设和积极互动累积起符号资本,再通过流量变现转化为经济资本,包括吸引广告商、品牌合作,从而转化为广告收入、带货佣金,也因此带来更多的社会关注和影响力,从而转化为社会资本。
社交媒体平台不仅为网红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是构建了一个网红与粉丝之间可以直接互动的环境。网红管理与粉丝的互动,通过评论区互动、直播连麦、私信回复等方式,让粉丝产生“被看见”的感觉。除了在直播中始终保持热情、耐心回复粉丝评论,频繁使用“宝子们”“宝宝们”“家人们”“老铁”这样非常亲昵的称呼之外,还会有很多博主刻意记住老粉丝的昵称并在直播中点名。这种细节的处理让粉丝感觉自己与网红建立了“朋友般”“家人般”的关系,这便形成了“准社会关系”。
“准社会关系”是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赫尔于1956年提出的概念,指一种单向的情感投入,常见于媒体用户对节目主持人或电视明星所形成的心理感觉。观众因为天天看电视而将电视明星视为自己的朋友,尽管他们与这些人物没有或仅有有限的互动。电视时代,观众的这种心理感觉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名人与大众之间的壁垒。社交媒体时代,粉丝更是从网红的反馈和互动中真切感受到自己与网红的关系是“朋友”或“家人”。虽然网红的回应属于职业性表演,未形成真正的双向关系,但那也比电视时代完全单向的情感投入更进了一步、深了一层。可以说,平台算法通过个性化推荐强化了粉丝的“被看见感”,加速了情感依恋的形成,而情感依恋又极大增强了粉丝为网红内容付费或者购买其推荐商品的意愿。
然而网红的这些行为正如同服务业中员工标准化的“微笑训练”,是网红产业的隐性职业规范,也是某种表演,其中包含了大量被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概念化为“情绪劳动”的劳动付出。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中提出情绪劳动“需要一个人去诱发或压抑情绪,以维持一种外在的仪态,从而使他人产生恰当的心理状态”,比如空乘人员为了满足乘客需求而进行情绪管理,让乘客感觉在一个快乐又安全的地方得到了关怀。
在网红现象中,情绪劳动成为常见的劳动形式,表现为网红持续投入情感来维系与粉丝的关系,例如展现亲和力、耐心解答问题、适时表达对粉丝的感谢和关爱等。网红甚至每天更新自己的衣食住行,与粉丝分享生活中的点滴。这种频繁的生活化互动,让粉丝在观看过程中会产生一种陪伴感和亲近感,仿佛在观看一个朋友的生活,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投入。这也培养出粉丝对网红的商业信任,促进其带货转化率。当网红被质疑时,粉丝也会基于这种情感联结而自发维护网红的形象,深信他们不会有错。
而对于粉丝而言,网红的存在能满足其多种价值需求。概括而言,有些网红生产的内容具有知识与信息价值,例如科普类、学习类、知识类博主,能在垂直领域满足人们相对小众但也很有意义的兴趣和爱好;有些网红整合大量信息,提供有价值的消费指导,如美妆、时尚、探店类博主;有些网红生产的内容具有娱乐与审美价值,例如才艺展示、幽默吐槽等,满足粉丝在闲暇时间的精神娱乐与审美需求;还有些网红的每日存在便对其粉丝具有情感与心理价值,成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寄托。
“网红—粉丝”文化中的“粉丝”,是一个舶来的学术概念,部分承袭自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勾连了对积极受众的研究兴趣,反映出学术界对文化消费的认识的转向。格雷等人认为,粉丝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次理论浪潮:第一波浪潮以费斯克和詹金斯等人为代表,关注粉丝对媒介文本的积极挪用、协商与有意义的生产;第二波浪潮研究粉丝作为社会群体的复杂性,关注粉丝群体内部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等;第三波浪潮关注粉丝个体的主体性和情感认知。而中国的粉丝现象另有独特的发展路径:起源于正在经历全球化与网络化的20世纪90年代,受到外来流行文化影响,融合了日本“宅文化”、韩国“偶像”文化和西方媒介粉丝的部分特征;随后又深受多方下沉话语和数字平台算法的“胁迫”,得到数字技术的赋权,同时也在算法与资本的合谋下,将粉丝实践嵌入了粉丝对倾慕对象的浓烈感情之中。
在网红现象滥觞后,“网红—粉丝”文化中的粉丝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们“粉”的并非大众媒体舞台上的明星偶像,而是在短视频和直播场景中的日常化的、更具亲近性的草根人设形象。网红与粉丝双方互动更频繁、更及时,粉丝的反馈甚至实时地影响着网红的言行,双方的情感联结与流量变现的距离也更近了。因此,在网红改写名人概念的同时,粉丝的意义也在被不断地改写和重建。值得注意的是,粉丝对网红的情感浓度也具有差异性。和传统的明星粉丝一样,“网红—粉丝”文化情境中的粉丝也可以被分为“路人粉”(casual fan)、“死忠粉”(cult fan)和“黑粉”(anti-fan),等等。
第二类是网红“人设”崩塌。粉丝对网红产生强烈的情感连接,源于人类普遍存在的名人崇拜倾向,即个体对公众人物强烈而执着的迷恋与投入。粉丝往往将理想、愿望投射到网红身上,如健身网红代表着健康自律,学习网红代表着学霸,这种投射成为粉丝情感寄托与自我认同的方式。但如果“宠粉人设”的网红私下辱骂粉丝,“节俭人设”的网红被爆出消费奢侈品,粉丝会立刻因失望而离开。这种“翻车”是粉丝对“真实感”的追求与网红“景观化人设”之间的矛盾。
“网红—粉丝”文化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带来了正面的社会价值。例如它推动了知识与文化的普惠传播,通过可随时触达每个普通受众的社交媒体平台,降低了知识与文化的接受门槛;它催生了以直播带货为代表的新经济业态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其中包括“三农”网红助力农产品销售,为乡村振兴与传统产业转型提供助力;它还推动了的线上生活参与,提升其技术自我效能感。例如“银发”网红在子女或孙辈的辅助下进行内容创作,实现了“代际反哺”和“代际互惠”,增强了家庭情感联结,也在与陌生人的互动中获得了精神回报;失能群体也能借助网红劳动增进亲社会性,并增进劳动者的福祉与获得感。
因为对网红的情感投射和认同,粉丝容易陷入盲目追随,包括在超出自己的经济实力的情况下模仿网红的生活方式,非理性地消费其推荐的商品;粉丝之间可能会攀比炫富,也有可能引发身材焦虑或外貌焦虑。网红为吸引流量而设计的争议性话题,也可能让粉丝形成扭曲的认知,将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合理化。更有甚者,当网红刻意煽动性别对立、圈层矛盾时,粉丝易被情绪所裹挟,在网络上大量传播夹杂着情绪与对立的观点。而当网红遭遇负面争议时,粉丝也可能在社群内压制质疑声音,互撕谩骂、拉踩引战,甚至演变为网络暴力的参与者,对批评者进行人肉搜索、言语攻击。这样的举动既损害了粉丝特别是未成年低龄粉丝的个体心智,也会对社会舆论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建构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针对这些负面现象,国家网信办近年来也持续部署了“饭圈”乱象的整治工作。
网红现象的蓬勃发展,无疑是数字时代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它改变了我们对“名人”的传统认知,提供了普通人实现自我价值和影响力的全新路径,也催生了诸如直播带货等新兴经济业态。然而,在“景观人设”和“流量至上”的逻辑上,网红与粉丝之间看似亲密的“准社会关系”实则蕴含着商业目的和潜在风险。当网红的行为触及法律红线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背离时,公众对其“名实相符”的期待便会破灭,曾经的忠实粉丝也随之人去楼空。因此,在享受网红文化带来的便利与乐趣的同时,我们也应保持清醒的判断,对网红背后的商业运作和潜在风险保持警惕,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负责任的网络生态。